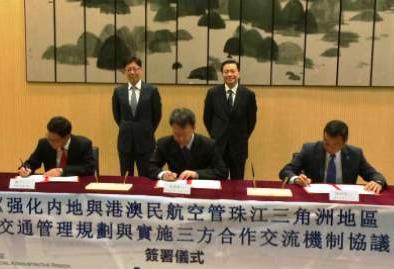劉光才:修修補補不能解決航線時刻緊張問題

這種情況不利于新航空公司和中小公司發展,缺乏經濟效率,限制了航空運輸業的競爭
最近,全球民航數據分析系統CADAS對全球103家航空公司運營效率進行了評估,南方航空以70.45%的放行、到港準點率排名第86位,而中國國際航空和東方航空分別以66.41%和64.46%位列第93、94位。
其實就在2009年以前,中國80%的航企航班都還能準點起飛,但后來這一數據逐漸下滑到目前的68.73%。
與之相應,近幾年中國航空運輸的客流量以每年兩位數的百分比增長。僅2014年,中國民航客運量達到近3.9億人次。
一方面是中國民航進入持續成長期,運量持續增長,運營飛機大量投入;另一方面是狹窄的空域、有限的民航航線時刻資源,使得機場擁擠和堵塞現象更加突出。由此,民航飛行正越來越多地受到空管系統的影響。
從目前的形勢看,不僅是首都機場、廣州白云機場、上海浦東機場等7大協調機場,一些中小機場也相繼提出時刻協調的申請,市場已經對現行的時刻管理體制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
有限的民航航班時刻與快速增長的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如何有效管理和分配航班時刻?現行的時刻資源分配機制如何與高速發展的民航業相匹配?為此,《瞭望東方周刊》專訪了中國民航大學民航發展政策與法規研究中心主任劉光才。

歷史身份優勢
《瞭望東方周刊》:目前航線時刻資源的分配情況是怎樣的?
劉光才:要了解中國的航線、時刻資源分配,首先要厘清三個概念:空域、航線、時刻。空域由軍隊系統——空管委員會負責整體協調;航線由民航局運輸管理部門負責;時刻由民航局空管行業管理部門管理,空管部門具體執行。
中國與歐盟一樣,采用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模式,也就是以行政配給為主,美國、韓國是混合管理體制,市場配置與行政分配相結合。自從2002年民航市場化改革后,從航線資源分配來看,我們的市場配置成分越來越大。除了來往北上廣三大城市的四大機場由政府控制分配外,其他都交給市場。
比如,在二三線城市不擁擠的機場,多是采用先到先得或者排隊規則來配置時刻資源,也不需要設立一個專門時刻分配委員會實施分配。如果出現需求沖突,由航空公司、機場、服務代理之間協調就好。對于航路空域而言,航空公司被分配到一個機場起降時刻資源,就默認地同時給予對應空中航路的時刻資源。
現在的關鍵是:繁忙機場的航線時刻資源越來越難拿到,新航空公司往往對此有抱怨。按照現有規則,航空公司在下一次重新分配時刻資源時,優先獲得本航季正在使用的航班時刻權利。
這意味著,時刻分配不是根據航空公司的支付意愿,而是以歷史時刻或“祖父條款”來分配的。這其實不利于新航空公司和中小公司發展,某種程度上缺乏經濟效率,限制了航空運輸業的競爭。
“時刻池”盡管給新進入者以50%的優先分配權,但是這一比例在總量中是非常小的,經常不超過10%,而且通常商業價值比較低,對于新航空公司而言是杯水車薪。
《瞭望東方周刊》:看起來,矛盾的關鍵還是航線時刻資源的稀缺,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
劉光才:表面來看是機場的設施保障能力提不上去。以首都機場為例,目前有三條跑道,而美國亞特蘭大機場有六七條跑道。我們為什么不多修第四條、第五條跑道,而是修建第二機場呢?
根源在于不管我們在地面修多少跑道,但飛機起飛的空中通道就那么幾條,空域有限的情況下,地面修再多也飛不上去。北京首都機場有3條跑道,連接著國內外近200條航線,卻只有11個空中進出口;上海浦東、虹橋機場共用8個空中進出口;像廣州白云機場、成都雙流機場、深圳寶安機場等,都涉及最關鍵的空中進出口嚴重缺乏、空域受限的問題。
民航業一直是中國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以兩位數,如15%、16%的速度增長,但空域的增長速度只有2%,剪刀差越來越大。所以民航業一直在呼吁空域管理體制改革,希望釋放更多空域給民航。
平衡大小航企的角色和利益
《瞭望東方周刊》:這么說,航線時刻緊張的關鍵是空域,這如何解決?
劉光才:在這個問題上,首先需要解決觀念的沖突。比如,美國明確空域是經濟資源,如何開發、利用、創造價值是其首要目標。他們的低空資源創造的價值為1000億美元,而中國不到100億元人民幣。
當然兩國國情不同。中國如何在保證國防安全的大前提下,釋放部分空域、極大緩解當前航路擁擠的狀況?
我個人的建議是:中國空域還有進一步合理利用的空間。根據現有軍方和民用空域使用情況還可以進一步細分。比如哪些是必須用的,哪些是經常要用的,哪些是基本閑置或使用較少的,然后確定空域分類管理政策。
《瞭望東方周刊》:回到航線和時刻問題上,目前關于航班時刻資源分配的市場化建議在理論上頗具吸引力,你怎么看?
劉光才:在現行航班起降時刻資源配置機制備受批評的背景下,國際上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府部門都在探索市場化道路。但大家研究了近20年,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繁忙機場真正實施時刻資源的自由定價和拍賣。
中國此前對航班時刻一直采用政府主導的行政配給方式。從理論上說,行政配給方式具有效率低下的天然缺點。對于航班時刻這種資源,理想的模式是通過市場方法配置,促進航空運輸市場競爭,提高對稀缺資源堵塞利用效率。但從實踐來說,中國還不適宜航班時刻市場化、高峰時段拍賣。
原因在于,中國航空公司普遍規模較小,缺乏國際競爭力,又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樞紐機場。因此在我看來,做大做強航空公司、構建樞紐型機場是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所以優先保證大型航空公司在協調機場的航班時刻比例是很必要的。
但同時,建立公平公正的航空運輸市場也是中國民航改革的基本目標,在保證大型航空公司利益的前提下,需要適當考慮中小航空的利益,比如在“時間池”中切出少量比例的時刻專供中小航空公司。
改革必須多舉并行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真正實現市場化需要哪些基礎性條件?
劉光才:從政策層面看,一方面,中國的民航產業剛進入成長期,市場機制還遠不夠成熟,產權、市場準入機制、價格、體制等改革還沒有真正到位。而中國航空公司市場還不是真正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行為的“非理性”決定了它還不能真正按照市場規律辦事,實行市場化不可避免會出現航班時刻價格“扭曲”的現象。
另一方面,航空運輸市場還不是一個完善的生產要素市場,資金、勞動力等市場要素還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動。而且,三大航各據一方,新進航空公司普遍規模較小,缺乏競爭實力,很難甚至根本不能與三大樞紐機場競爭。
在市場化這個問題上,現在還處于爭論階段。我個人傾向于走第三條道路,也就是一級市場行政分配,二級市場交易。航空公司從政府手上拿時刻,有的拿得多、用不了,或者有的覺得資源配置不合理,在二級市場既可以交換,也可以市場交易,實現有限的市場化。
總之,只有民航改革發展到一定程度,航空公司產權結構多元化、擁有定價自由和競爭日趨激烈時,才能從航班時刻行政分配過渡到市場化配給。
《瞭望東方周刊》:近年來主管部門一直在改善航線時刻資源分配機制,你認為還有哪些改進空間?
劉光才:應該說從2000年開始,航線時刻資源分配機制一直在進步。每到航季航班分配時,運輸管理部門會出一個小冊子,分配細則有哪些,指導思想是什么,分配原則、分配程序等都會一清二楚地列出來。可以說,公開性、公正性正越來越好。
當然,仍然存在改進空間。比如,在每年的全國民航航班時刻協調會中,分配優先政策,國際、國內航班時刻分配比例,新增航班時刻分配的動態變化信息等,細化到每個航空公司的具體分配時刻,包括不分配給某申請公司的原因、協調機場新增時刻分配比例、分配結果等都要形成信息公開化制度。
或是建立一個航班時刻先期自行協商機制,充分調動航企積極性,節約國家行政資源。
總的來說,我們現在已經無法靠著對現有航路進行修補,或者從現有容量中挖掘潛力來解決問題了。改進航線時刻分配機制、增加航路,增加終端空中進出口,加強機場基礎設施建設,提升運行保障能力等多重改革措施齊下,才能讓中國民航保持當前的發展速度。
責編:admin
免責聲明:
凡本站及其子站注明“國際空港信息網”的稿件,其版權屬于國際空港信息網及其子站所有。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轉載使用時必須注明:“文章來源:國際空港信息網”。其他均轉載、編譯或摘編自其它媒體,轉載、編譯或摘編的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站對其真實性負責。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轉載使用時必須保留本站注明的文章來源。文章內容僅供參考,新聞糾錯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