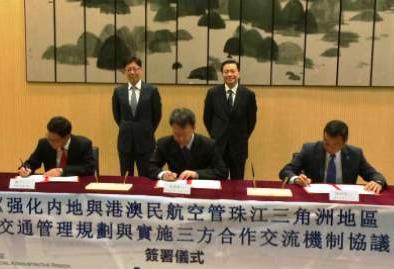陳迎春:“C919飛機自主創新有五個標志”
據中國商飛大型客機C919項目常務副總設計師陳迎春介紹,C919飛機自主創新有五個標志:第一,飛機的總體方案自定;第二,氣動外形由中國自主設計、自己試驗完成;第三,飛機的機體從設計、計算、試驗、制造全是中國自己做的;第四,系統集成由中國自己完成;第五是中國自己的特色管理。
陳迎春畢業于西北工業大學飛機系空氣動力學專業,1983年進入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飛機設計研究院工作,曾參與和主持了“飛豹”、 MPC-75、AE100、ARJ21、C919等多種型號的軍用、民用飛機的研制和國際合作。2008年中國商飛成立后,陳迎春擔任C919項目常務副總設計師。
圍繞大型客機C919的研發,陳迎春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的專訪。
“舉全國之力”研制大飛機
《21世紀》:中央下決心實施大飛機專項,最重要的原則是“設計并制造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國際競爭力的大飛機”。C919大飛機的研制設計首先從哪里開始?
陳迎春:2008年5月中國商飛公司成立,揭開了中國人自己的大型客機的研制序幕。商飛是一家新公司,技術力量主要來自上海飛機設計院(之前的640所),并沒有多少設計人員。中央決策的時候已經明確,要“舉全國之力”研制大飛機。所以在初始階段,從全國12個省市的40多家單位,召集了將近500名設計人員集中在上海,成立了大型客機聯合工程隊(Joint Engineering Team,JET)。
2008年7月,中國大飛機項目啟動,第一步要做的是可行性研究和初步技術方案論證。我們的設計分兩步走:首先是做初步技術方案設計,也叫聯合概念設計(Joint Concept Design,JCD)。要大致描述大飛機的輪廓,飛機裝多少人,裝多少貨,飛多遠,飛機的尺寸,裝什么樣的發動機與系統,確定發動機的量級,電源的功率等,篩選供應商。初步方案設計用了半年時間。
2009年開始第二步,做系統聯合定義設計(Joint Define Design,JDP)。這個階段主要是向供應商描述我們將制造一個什么樣大飛機,就像我們做衣服,要與裁縫描述顏色、尺寸一樣,告訴他們發動機和系統的要求等。與第二步并行進行的是,我們自己開始做氣動、結構強度和系統方案初步設計,通過仿真計算分析、制作模型、做風洞試驗和結構強度試驗等,逐步確定飛機的氣動外形和結構。這個階段也叫初步設計(Preliminary Design Plan,PDP)。這兩個階段是同步進行的。我們原來計劃使用兩年時間完成系統聯合定義(初步設計),而實際上用了三年時間。
所以到2011年12月,飛機設計通過評審(Preliminary Design Review ,PDR),2012年初開始進入到詳細設計階段(Detailed Design Plan,DDP)。
概括說,飛機設計要經過總體方案設計、初步設計、詳細設計三個階段, 然后進入生產制造和試驗試飛。目前大型客機就要下線了,后面還要進行系統的安裝測試,地面試驗完成后,再進行空中飛行試驗。
國產大飛機之路一波三折
《21世紀》:您之前的工作經歷是設計殲擊轟炸機,從什么時候開始進入民用飛機設計領域?
陳迎春:是1988年。1987年,前西德主要的航空企業梅塞施密特-伯爾科-布洛姆公司(Messerschmitt-B?lkow-Blohm,MBB)提出與中國合作研制代號MPC-75中型噴氣式支線客機。當時這家公司還沒有加入空客,正處于猶豫狀態,后來他們決定與中國合作,中德雙方組建了合資公司,目標是合作研制。MPC-75性能相當先進,有座位70-80個。當年4月,中德雙方在漢諾威展覽會上聯合展出了這架飛機模型,向全世界公布了這一消息。
我國自“運10”下馬后一直希望再次進入噴氣式客機制造領域,能有這樣的合作機會當然很高興。所以自1988年底,中方前后派出了幾百名技術骨干前往西德。我是1988年底第一批被派到西德學習和工作的,我們這一代很多飛機設計師都曾經參與這個項目,包括C919總設計師吳光輝。
這個項目從1987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91年,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這是我從軍機轉向民機的開始。正是在MBB的工作,我第一次接觸民機設計,很遺憾這個項目沒有進行下去。
1991年中國與美國麥克唐納·道格拉斯飛機制造公司合作,在上海建立了MD-82飛機的組裝廠,當時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組裝生產上。
《21世紀》:但是MD-82飛機項目因美國麥道公司破產徹底告吹。
陳迎春:我1989年回到中國繼續從事軍機研制,直到1995年又遇到一次參與民機研制的機會。這一年中國與波音合作,是由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四國聯合的飛機設計項目。那時歐洲的空客嶄露頭角,亞洲的中國、日本、韓國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美洲有波音,歐洲有空客,亞洲有什么?有人倡議亞洲國家聯合起來搞一個噴氣式客機“亞洲快車”AE100(Asia Express)。但是亞洲沒有聯合體,中日、韓日之間關系復雜,聯合設計飛機很難談攏,所以才有了美國波音出面搓合,把三個國家的設計師請到了美國。
當時波音拿出B737-600的設計方案,并表示,你們不用再設計了,就把這款現成的設計改名成AE100。如果這個方案成立,波音將用這款飛機占領整個亞洲市場,在亞洲徹底打敗空客。
這件事在當時對中國而言可以說是一個重新進入航空制造領域的捷徑。但是這個項目最終也沒有做成。
此后,歐洲空客向中國拋出橄欖枝,讓我們到他們那里合作設計飛機。我們派了一撥人到圖盧茲兩年,卻并沒有聯合設計這回事,實質性的設計并不讓中國人參與。
1999年發生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事件后,軍機的發展進入快車道。直到2002年,國務院批準ARJ21-700飛機項目立項;2008年5月,國家組建中國商飛公司,作為大型客機項目的實施主體。中國的大飛機之路一波三折。
《21世紀》:歷史沒有如果,我們曾經一次次地與成為航空工業大國的機會失之交臂。
陳迎春:我從大學畢業到現在已經32年,經歷了國家航空制造大發展的時期,之前是軍機大發展時期,現在是客機的大發展時期。我們為什么要發展民用機?根據《航空周刊》推算,2015年到2019年,全世界(除中國外)戰斗機的市場是842架,產值是872億美元;而客機市場是10099架,產值是1.37萬億美元,客機的產值大約是戰斗機的16倍,差距巨大,說明客機是現代航空的“主戰場”。
中國航空市場客貨運量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我們需要客機,自己不搞就得買,除了花錢多之外,還要處處受制于人,我們有刻骨銘心的教訓。
C919完全是自主設計
《21世紀》:有一種觀點認為,無論ARJ21還是C919都是系統集成,這可以稱之為自主創新嗎?
陳迎春:系統集成本身就是集成創新。對于復雜的大型系統,如航電、飛控系統等,我們是拆成子系統讓外國公司做,而系統的集成是我們自己做的,雖然增加了難度,但對掌握技術是有提升的,為以后開發新型號積累經驗。這就像到超市買速凍餃子,這次吃飽了,下次還想吃依舊不知道餃子怎么做,但是當你買來面粉、肉,再和了面、搟了皮,自己做了一遍后,就知道怎么包餃子了。研發C919相當于我們自己包了一次餃子,但是面、肉是到市場買的,我們自己既沒有養豬、種菜,也沒種小麥。道理就是這樣。當然我們要通過C919項目帶動國內“養豬、種菜、種小麥”的行業,避免被別人的“肉、菜、面”卡住而做不成我們自己的“餃子”。最終形成國內外合理布局、有序競爭的供應商體系。
《21世紀》:這是一種能力的獲得。在全球資源配置的條件下,能力的獲得比技術本身更重要。設計師在具體設計一架大型客機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是什么?
陳迎春:初步方案設計應該是最關鍵的,要確定方向,比如飛機布局是什么樣的,所謂布局就是機翼、機身、尾翼、發動機、起落架,這幾大部件的相互關系叫布局。再一個是航程、座級基本的參數,當確定飛機尺寸、坐多少人以及飛多遠,最后確定發動機的功率,用多少電。總設計師或者總體設計就是這樣開始描述飛機的構思內容。就像我們蓋房子,先要有個構思,房子要蓋幾層,蓋個什么樣式的,使用什么建材,這些大的構思很重要。
《21世紀》:關于技術路線,特別是自主研制,國外研究機構有些質疑,他們列舉ARJ21機翼請烏克蘭幫助設計,并揣測C919并非完全中國自主設計。
陳迎春:在C919項目設計上,我們一分錢也沒給外國人,我可以負責任地說,C919完全是自主設計。
我負責ARJ21的氣動設計,我們曾與烏克蘭安東諾夫飛機制造公司簽署了幫助評估的協議,另外也邀請過一些專家參加咨詢,其中幾個骨干現在都加入了中國商飛,但是這款飛機是我們自己設計的,所以國外機構的說法并不準確。
參與C919設計研制的工程技術人員目前共有3000多人,包括外國雇員300多人。比如當時做機翼設計時,我們集中了國內從事飛機氣動專業頂尖100名專家,組成8個隊,設計了500多副翼型,在計算的基礎上選了8副翼型進行風洞試驗驗證,從中選出4副進行機翼設計,再組成4個隊,按照同一個目標和要求同時開工,拿出第一輪成果后相互評議。在總結四個方案設計的優點后合成一個更好的。在此基礎上,再進行驗證。最后才確定現在用在飛機上的這1副機翼。
這副機翼不僅在國內做試驗,還到歐洲(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荷蘭)、美國做試驗,所有試驗的結果均顯示,我們飛機的幾項重要指標比競爭機型都好,比如升阻比、巡航特性、失速特性、噪聲水平、結冰特性等。對此,國內外同行是高度認可的。
《21世紀》:自主設計,或者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創新的標志是什么?
陳迎春:概括說,C919飛機自主創新有五個標志:第一,這個飛機的總體方案是我們自己定的,沒有任何外國人參與;第二,氣動外形是我們自己設計、自己試驗完成的;第三,飛機的機體,從設計、計算、試驗、制造全是中國人自己做的,西安、沈陽、成都、哈爾濱、南昌等地全都參與了;第四,系統集成是我們自己完成的;系統集成并不是意味著把國外的系統或者材料買回來就能變成飛機,否則如何解釋全世界目前能進入客機研制領域的只有歐洲、美國、中國、俄羅斯、加拿大、巴西和日本?第五是中國自己的特色管理。我這里說的“自己”不僅是中國商飛,還包括國內各行各業為C919做出過貢獻的人們,我們真正做到了“舉全國之力”。
如何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21世紀》:C919即將下線,一旦進入市場,競爭的型號是誰?
陳迎春:C919瞄準的競爭機型是B737和A320。C919從設計角度在幾個方面具有優勢:比如機身更寬,使用新一代發動機,選擇了全電傳操縱系統,最先進的綜合化模塊式航電系統,等等。
當C919樣機2010年出現在珠海航展時,兩大公司看到C919的設計超過B737和A320就坐不住了。但那時波音與空客正處在困難時期,所以采取了折中的措施,空客決定A320換一個與C919同樣的發動機,后來波音也為B737換了同樣類型的發動機。但它們的機體還是老的,主要系統也沒變。
C919現在有500多架訂單。我們最初的設想是希望占到新增飛機6000架的5%,現在已經突破8%以上,已經超出預期了。C919下線后這個數字還會增加。
《21世紀》:飛機型號的市場壽命取決于什么因素?
陳迎春:所有的飛機產品都是根據市場競爭決定銷售時間的長短。我把幾個型號的飛機分別叫“萬歲機”和“千歲機”,“萬歲機”是指一個型號的飛機可以賣到萬架以上的,目前只有波音737和A320實現了銷售了萬架以上的紀錄;“千歲機”也不少,比如波音747、757、767、777都賣到千架以上;而空客既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早期A300銷售了500多架,A330也是“千歲機”,但是A340只賣了200多架就停產了。
C919能在市場上存在多久,第一是與我們自己有關系,比如生存能力,即受客戶歡迎程度;第二是與競爭對手有關系,比如波音767原本是一個很好的機型,但A330一出來就被打敗了,最后只能停產,甚至還有退貨。而波音787面世,A330就面臨險境,兩家航空公司都在進行有針對性設計,用獨有特性打敗對手。
我們預判,C919的優勢將會保持很長時間。第一步先進入“千歲機”的行列,這就是一個成功。實現銷售萬架要用很長的時間,波音737從上世紀60年代一直賣到現在,每年平均銷售在200架左右。A320的銷售速度上升比波音快,基本上每年銷售300架,所以空客比波音在更短的時間內達到了這個數量。
《21世紀》:在發展大飛機的半個多世紀里,中國錯過了很多機會,商飛未來如何與百年老店波音競爭?
陳迎春:波音的百年實際包括軍機制造部分,重要的是看民機的發展,他們也就是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這是什么概念?波音研發民機時我們也開始著手了,1970年我們的“運7”首飛上天,這是我國在前蘇聯安-24型的基礎上研制生產的雙發渦輪螺旋槳中短程運輸機。
空客是在上世紀70年代才發展起來的,我們的“運10”也是上世紀70年代啟動的,比空客只晚了三年。
上世紀80年代巴西航空業起步,而我們在進行MPC-75合作開發。上世紀90年代加拿大的龐巴迪崛起,同期我們在做AE100。
我們每一次機遇都趕上了,每一次都想大展拳腳,但是前面幾次最后都沒走下來。直到2000年俄羅斯航空工業搞SSJ-100的時候,中國的ARJ21起步,開始自主研制。目前馬上就要交付給航空公司運營。
航空制造業外的人很難體會我們的痛苦和忍耐,盡管如此,制造中國自己的大飛機的信念一直在,而這次我們終于成了,中國這代航空人終于迎來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現在國家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有較強的科學技術實力支撐,中國的制造工業水平正在由大變強,這些都是支撐中國大飛機項目的基礎。C919讓我們更加有信心,未來再把發動機和系統的短板補上,那時,我們一定會從航空大國變成航空強國。有了ARJ21和C919鍛煉成長起來的隊伍和形成的基礎,在我們研制寬體客機的時候,一定會更快更好。
責編:admin
免責聲明:
凡本站及其子站注明“國際空港信息網”的稿件,其版權屬于國際空港信息網及其子站所有。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轉載使用時必須注明:“文章來源:國際空港信息網”。其他均轉載、編譯或摘編自其它媒體,轉載、編譯或摘編的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站對其真實性負責。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轉載使用時必須保留本站注明的文章來源。文章內容僅供參考,新聞糾錯 [email protected]